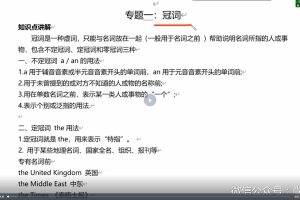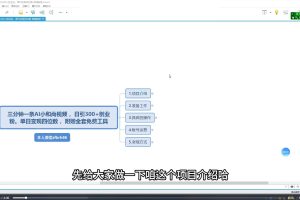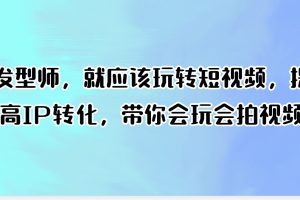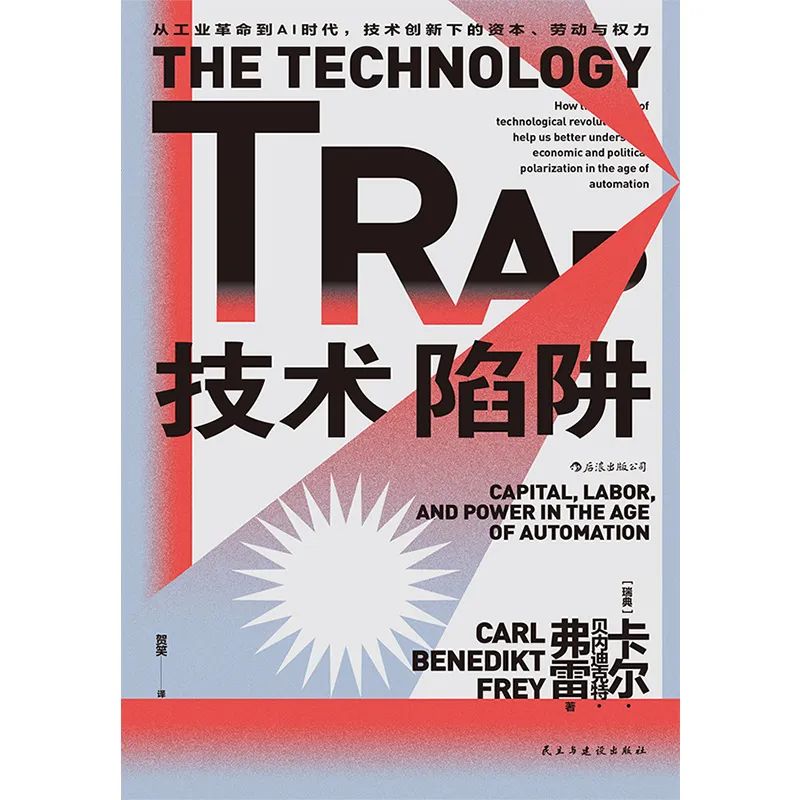
“如果没有那600位灯夫,1900年时夜晚的纽约城就只能由月光照亮。他们拿着火把爬上梯子,确保行人离开家以后走在街上,不至于只能看到不远处燃着的雪茄。”在《技术陷阱》一书的开头,瑞典经济学家、牛津新经济思维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雷以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20世纪初夜幕降临纽约城时,“华灯初上”这个词背后已被人遗忘的“灯夫”职业。
“灯夫”消失
“灯夫”这个词汇最后一次成为新闻头条,或许是在1907年4月24日:曼哈顿街头2.5万盏煤气灯中绝大部分都没有被点亮——灯夫们在这一晚罢工了。到了晚上9点,只有中央公园里少数东西走向的马路有亮光,因为那儿是由电灯照亮的。
自1414年伦敦第一批街灯亮起,灯夫这一职业就存在。随着电力发明和应用,油灯和煤气灯逐渐被更加安全、高效的电灯取代。纽约在19世纪后期就安装了第一批用电的路灯,但由于每一盏灯都有一个开关,必须手动开启和关闭。事实上早期的电气化只是让灯夫的工作更加轻松,让他们不再需要带着长长的木杆火把逐一电量路灯。
“那一年以点灯为业的人是不幸的”,弗雷如此写道。灯夫归根结底并未成为简单化、自动化的技术进步的受益者。点灯这一曾经能让一个工人养家糊口的技能变得非常简单,小孩子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就能随手开关电灯。更为致命的是,一位灯夫每晚最多能处理50盏灯,而如今一位变电站员工能在数秒内开启几千盏灯。到了1927年,随着纽约最后两名灯夫放弃这一工作,灯夫这一历时500多年的职业就此终结。
不少人曾乐观地认为,技术创新的蓬勃发展可以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富有、更平等,那么少数灯夫丢掉工作又有什么关系呢?抱持这一想法的顶尖学者也不在少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发现,20世纪经济学领域的所有进展几乎都要归功于技术。另一位诺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也坚信,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美国的不平等状况已自动减少。
换言之,如果多数人能享受到进步的好处,整个社会就会愿意牺牲少数败给了技术进步的人。技术提高了绝大多数工人的生产力和生产技能价值,也让民众作为一个整体获得更高收入。即使对于那些在和机械化的角逐中失去工作的人来说,或许也有大量体力要求更低、工资更高的工作可以选择。
遗憾的是,“如果牺牲者数量更多,我们还会这样想吗?如果大部分被取代的工人都只能找到工资更低的工作呢?”在弗雷看来,任何人都无法随意假定技术必定能在仅仅牺牲少数人利益的情况下造福多数人,而当大部分人被技术变革甩下时,抵制变革就会是自然而然。
我们对当前时代的迷恋、对新技术带来的许诺与危险的关注,常常会让我们觉得自己的体验是全新的,但历史其实往往在变调和押韵中重复自身。事实上,时代的悖论与反转已经悄然发生。比尔·盖茨在2012年就指出:“创新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快……但美国人对未来的悲观更胜以往。”出生在1940年的美国人有90%比父辈更富裕,但1980年出生的美国人中只有一半比他们的父母更富有。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如今只有略多于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仍相信孩子会比自己这一代更富有。
增长落差
经济学家将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分为使能型技术(enabling technology)和取代型技术(replacing technology)。二者的区别在于,取代技术让工作和技能变得多余。相反地,使能技术会帮助人们更高效地完成已有的任务,或为劳动者创造全新的工作机会。灯夫、纺织工人、电梯操作员、码头和铁路搬运工等工种,因为取代型技术的产生而消失,电力、电器等使能型技术则在更大范围内推动了全社会效率和福祉的提升。

取代型技术的发展是否受阻,取决于谁会从中获利和政治权力的社会分布情况。罗马皇帝提比略由于害怕愤怒的失业玻璃工人造反,非但没有奖励发明了摔不坏的玻璃的人,反而把他处决了。另一位罗马皇帝维斯帕先也拒绝使用可以运送巨大沉重圆柱的机械装置,因为它可以节省数千名工人的劳动力,但却可能因为造成失业而带来政治不稳定,“用它怎么能养活我的子民呢?”可以说,“让技术维持现状以保留工作,这一选择在政治上更具吸引力”。
当然,稳定治理未必简单等同于保障就业。古登堡在发明印刷机后,很少有抄写员和篆刻员反对印刷术——他们要么专门抄写用印刷术不划算的短文稿,要么转行成了收入更高的装订员和设计者。但由于担心识字的人会削弱其统治地位,苏丹巴耶济德二世在1485年颁布法令,禁止在奥斯曼帝国用阿拉伯文印刷。
弗雷指出,经济史和技术史告诉我们的重要一点是,技术进步对收入的影响程度决定了人们对它的态度。以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伴生了“工厂”“铁路”“蒸汽机”和“工业”等新词的出现,同时也首次出现了“工人阶级”“罢工”和“贫困”等词汇,并催生了许多政治上的变革。
在工业化初期这一“典型的工业革命时期”,产量的增长速度几乎是工资增长速度的四倍,增长带来的收益绝大部分归了资本所有者。19世纪的前40年,由于土地和劳动占收入的份额都在下降,国民收入的利润份额翻了一番。工业家在这个时期“依靠广大工薪阶层的苦难而变得富有”。只有在苦熬过六七十年后,“普通人才真切体会到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惠及自身”:在1840年开始的60年内,工人的人均产量增加了90%,实际工资则提高了123%。
在弗雷看来,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完善、英国政府订立最低工资标准、劳工运动的兴起和工会的议价能力提升等各种因素,都无法完全解释这一工业化进程中工资的滞后上涨现象。经济学理论认为,如果技术取代了现有任务中的劳动力,薪资和劳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可能会下降,同时资本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逐渐增加,带来产量提升与“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实际工资”之间的落差;相反,只有使能型技术才能在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创造和增加劳动力需求。
时代的变迁放置在每一个个体、群体和世代身上的压力都是不均等、不平衡的。由于营养摄入不足,1850年出生的英国男性比1760年的男性更为矮小——“整整三代普通英国人的生活水平都已经下降”,第一次工业革命采用的是取代型技术,带来了大规模失业、贫富悬殊、劳动者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甚至恶化等诸多社会问题。相反,使能型技术能较好地平衡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因此以内燃机和电力的大规模应用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美国并未受到太大的抵制。
未来的警钟
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说过:“经济萧条、失控的通货膨胀或者内战都能让一个国家变得贫困,但只有生产率会让它变得富有。”遗憾的是,以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未必是使能型技术的时代,却很可能是取代流水线工人的技术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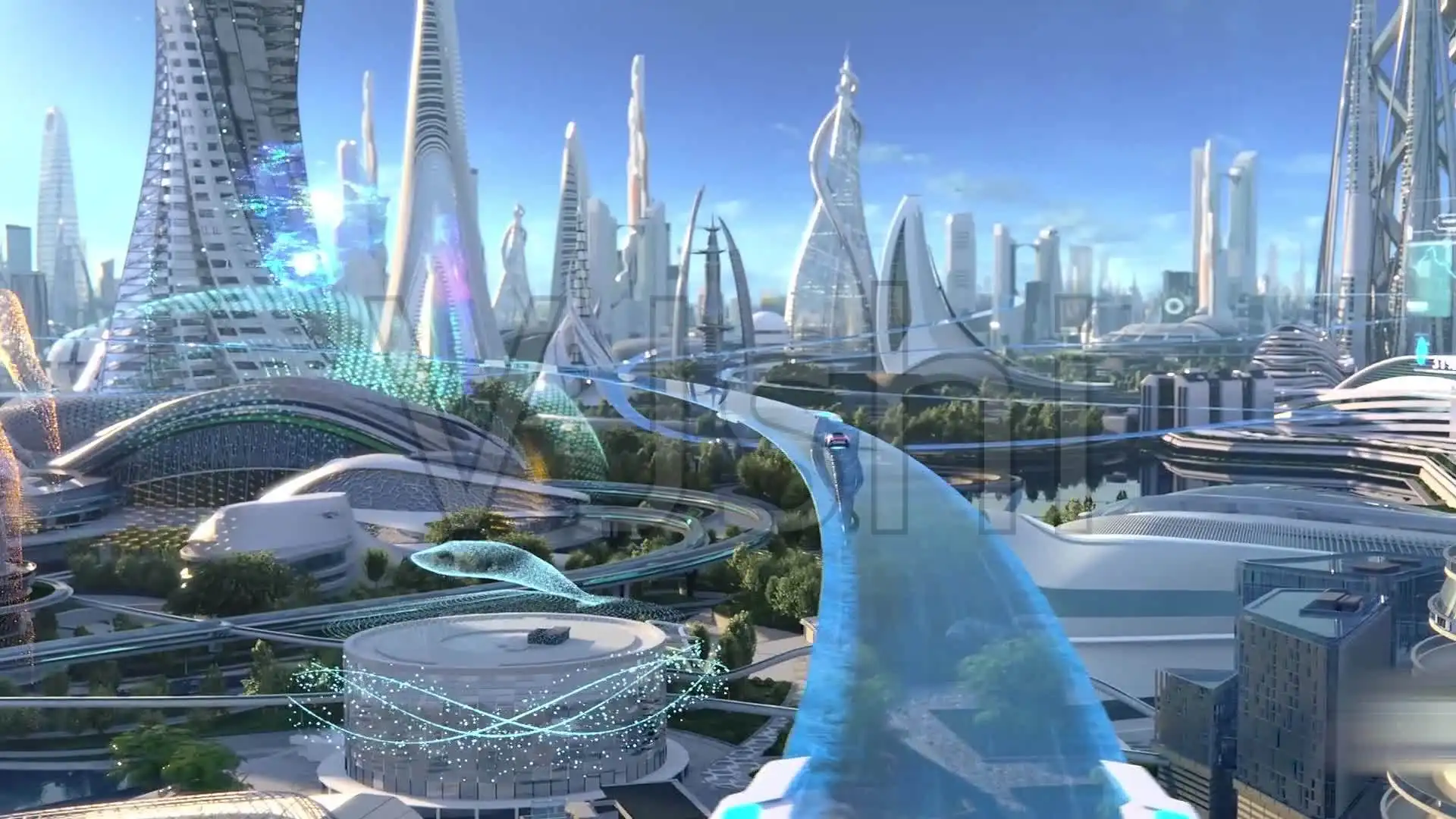
在弗雷看来,机械化工厂代替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体系,传统中等收入工作机会消失,劳动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下降,利润飙升,最终收入差距急剧扩大。计算机时代不平等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技术、新经济让经理、工程师、律师、科学家、记者、咨询师和其他知识工作者等等“符号分析师”这一新阶层从中获益,提高了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与此同时,随着中等收入的常规工作岗位不断减少,非技术型的劳动者被迫向低薪服务型岗位转移,使得欧美国家橄榄形的传统中产阶级社会滑向“两头大、中间小”的收入与财富分布形态。
哪怕传统意义上的创作型、创意性高薪白领工作也未必安全。计算机出版使文字排版成本更低、用途更广,但在计入通货膨胀的因素后,拥有更多新技能和新职责的平面设计师的时薪,也仅仅比1976年的普通印刷工人高出约一美元。这是因为印刷设计师取代了印刷工人,但网页设计师又部分取代了印刷设计师,随之又逐渐被手机用户界面设计师取代——技术正在不断重新定义什么是出版以及该如何出版。每一次变化都带来了新的专门技能需求。
更令人忧心的是,工作的出现与消失的分布极为不均衡:在服务经济迅速增长的地区,每一个新的技术岗位有望创造足够的需求来支持另外五个新的就业岗位;相比之下,传统制造业地区每失去一个蓝领工作岗位,就有可能让当地同步消失1.6个服务业工作岗位。用哈佛大学教授、城市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的话来说,如果技能型城市继续迅速发展,同时制造业与工业市镇不断衰落,“我们将可能看到一个发展更不均衡的美国。富有、成功且技能程度高的地区将在世界范围的竞争中取得胜利,贫穷、技能程度低的地区则将成为绝望的温床” 。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从经济角度来看,自动化时代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早期工业化的镜像而已。人工智能、移动机器人、无人机等下一阶段的技术突破或许可以再次提升劳动生产率,问题在于这些技术中许多都是取代技术,因此它们会进一步给非技术型工人的工资带来下行压力,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分配极有可能更为不均。
如果我们不解决自动化过程中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的问题,我们的社会将付出巨大代价。弗雷提出,为避免落入技术陷阱,各国政府必须出台政策刺激生产率增长,同时需要采取教育改革和加大教育投资、提高低收入家庭的福利等多种措施,努力降低自动化的社会成本。
无论弗雷提出的方案是否适用,毋庸置疑的是,在一个技术创造了很少的就业机会却创造了巨大财富的西方社会,未来的挑战发生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而非技术领域,最大的危险是不公正、不公平的收入分布与财富分配,以及极有可能随之出现的激进思想与民粹主义。在美国和欧洲,在那些工作越是容易被自动化取代的地方,人们对民粹主义的热情越高。
早在1965年,《纽约时报》就曾对计算机革命发出警告:“一群具有技能的美国人被剥夺了意义和价值……”。西方社会解决结构性困局的根本出路,或许只能在于努力实现公平共享的、可持续的、有民众参与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声明:本站所有资源版权均属于原作者所有,这里所提供资源均只能用于参考学习用,请勿直接商用。若由于商用引起版权纠纷,一切责任均由使用者承担。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我们进行处理,邮箱:502212423@qq.com。

 成为VIP
成为VIP